網(wǎng)絡結(jié)構(gòu)與傳染


1347—1352年前后,腺鼠疫(俗稱黑死病)緩慢但持續(xù)地在歐洲蔓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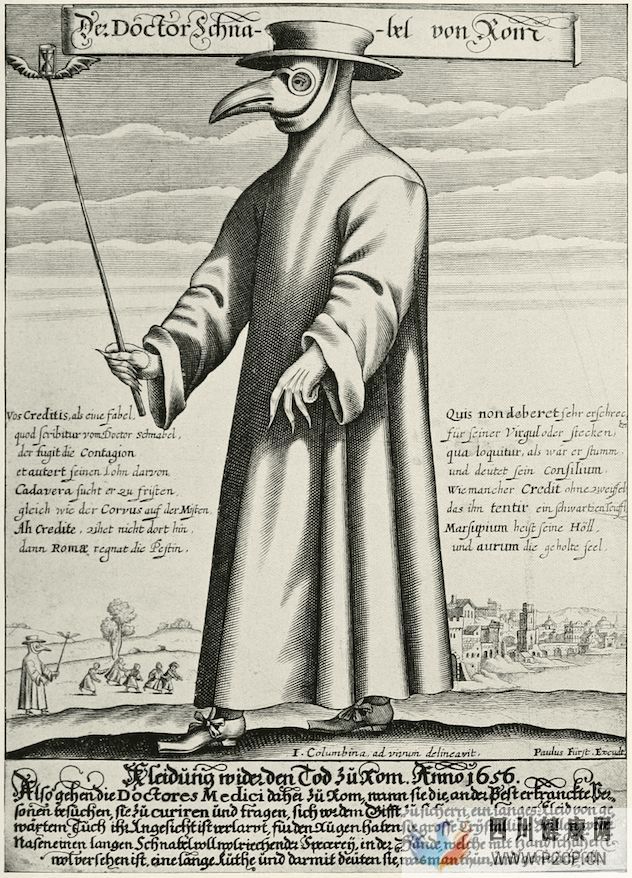
罪魁禍首——鼠疫桿菌——是由跳蚤攜帶的病原體,在它們吸食感染者的時候攝入。這種桿菌會堵塞跳蚤的消化道,使它們更加渴望營養(yǎng)物,從而貪婪地繼續(xù)覓食,將桿菌傳染給更多宿主。跳蚤很適應寄生在老鼠、人類和其他動物身上,某些抵抗力強的宿主充當細菌攜帶者,其他一些則在被叮咬和感染后很快死亡。這種疾病非常可怕:開始像流感那樣令人衰弱和發(fā)燒,但很快轉(zhuǎn)為大范圍出血。壞死的組織呈現(xiàn)黑色,從而有了“黑死病”的名稱。
當時的衛(wèi)生條件、對傳染病的認識不足,以及人類和許多動物接觸密切,共同導致這種疾病對中世紀的勃興城市帶來致命的打擊。它使巴黎和佛羅倫薩的人口在兩三年內(nèi)減少了大約一半,漢堡和倫敦等城市的死亡人數(shù)更多。現(xiàn)在我們認為,黑死病是從中國沿著絲綢之路傳到君士坦丁堡,然后在1347年隨著熱那亞的商船進入西西里島,很快消滅了島上近一半的人口。此后疾病繼續(xù)蔓延,沖擊意大利部分地區(qū),此后是馬賽,再擴展到整個法國和西班牙,最終在幾年后進入北方的一些國家。總體上,黑死病估計殺死了超過40%的歐洲人口,在抵達歐洲前還在中國和印度奪去了約2500萬人的生命。
從現(xiàn)代視角來看,真正令人驚訝的是這種疾病蔓延的速度緩慢但又有條不紊。雖然黑死病的傳播偶爾會出現(xiàn)遠距離跳躍,例如沿著絲綢之路等貿(mào)易路線或者通過航船,但它在整個歐洲的推進平均來說每天卻只有約兩公里,即便以當時的徒步旅行標準看也相當緩慢。盡管黑死病很少在人與人之間直接傳染,但卻是隨著人類活動而蔓延——通過寄生在船艙的老鼠、農(nóng)場牲畜和人類身上的,以及躲藏在衣服中的跳蚤——因此這種瘟疫的傳遞是依賴人類網(wǎng)絡以及人類周圍的各種動物。
黑死病的緩慢傳播告訴我們,中世紀時大多數(shù)人類的移動和交際范圍是多么有限。現(xiàn)代的傳染病大不相同,傳播極其迅猛,通常在幾周甚至幾天之內(nèi)就跨越不同的大陸。2014年通過在南加州一家美國主題公園的接觸而在未接種疫苗的成人和兒童中暴發(fā)的麻疹,幾天后就出現(xiàn)在數(shù)百英里外的學校里。2015年暴發(fā)的埃博拉病,在一周內(nèi)便由塞拉利昂的醫(yī)療工作者帶到歐洲和北美的城市。
本章我們將看到,傳染和擴散如何受到網(wǎng)絡結(jié)構(gòu)的影響。除對于疾病傳染的深入探討外,這方面的認識還將提供一個起點,以理解觀念、金融情緒以及就業(yè)和工資的不平等性等更為復雜的傳播現(xiàn)象——它們將是后續(xù)各章的主題。
傳染與網(wǎng)絡結(jié)構(gòu)
我們今天的許多網(wǎng)絡與中世紀的人際網(wǎng)絡當然有巨大差異,但從一種特殊類型的現(xiàn)代網(wǎng)絡中,我們?nèi)阅軐W到與黑死病緩慢而頑固的蔓延有關的許多原理。
圖1描述了美國一所高中青少年的浪漫關系(或者說性關系)網(wǎng)絡。學生記錄的是18個月中的交往關系。
在該圖描繪的網(wǎng)絡中,典型的學生只有一個或兩個交往對象,可是該網(wǎng)絡依然出現(xiàn)了一個“巨型分支”(giant component):圖的左方的巨大相連部分,包含通過一系列相互關系而連接起來的288名學生。
圖1 美國中西部一所高中里的人際網(wǎng)絡,來自Add Health數(shù)據(jù)庫。圖中的節(jié)點代表各個學生,顏色代表性別。每條連線代表在18個月的時間內(nèi)存在戀愛或者性關系。某些分支旁邊的數(shù)字代表這類分支出現(xiàn)的次數(shù),例如,有63對學生只在他們相互間存在關系。孤立的學生沒有顯示在圖中。有剛好超過一半的學生處于圖左方的一個巨大分支中。對本圖中的數(shù)據(jù)首先加以分析和探討的研究成果是Peter Bearman,James Moody and Katherine Stovel(2004)。
“分支”是一個網(wǎng)絡的各個部分,其中的每個節(jié)點都能通過一條聯(lián)系路徑到達彼此。圖1中有剛好超過一半的學生處于巨型分支中,其余分屬許多小型分支。有超過四分之一的學生報告說沒有戀愛關系(大家應該都記得高中的寂寞時光),這些人并未顯示在圖中。
該圖凸顯了一個危險:盡管平均而言每個學生只有很少的交往對象,但性傳播疾病卻可能蔓延到很大一部分群體。圖中的每個連接都代表疾病從一個人傳染給另一個人的可能性。如果巨型分支中的某個人染病(例如通過與校外的某人交往),疾病就可能在這一分支乃至整個學校中廣泛傳播。
例如,HPV病毒(人乳頭瘤病毒)就是通過性傳播,可能導致宮頸癌等幾種癌癥。HPV病毒的一個危險在于,它通常是無癥狀的,被感染者沒有理由認為自己染病,從而可能繼續(xù)把病毒傳染給其他人。據(jù)估計,大約有40%的美國成年人攜帶HPV病毒,其中許多人并無意識。大多數(shù)被感染者對性關系的態(tài)度并不隨意,他們只是碰巧成了巨型分支的一部分。
圖1中,我們能一眼看出為什么疾病的傳播可能比較慢,因為每個人的連接數(shù)量較少。可是通過巨型分支,最終仍能達到很高的感染率,正如當年的黑死病那樣。
從圖中還能看到,疾病的傳播并不依賴有濫交者或性工作者的存在。連接度較高的人可以放大和加快疾病的傳播,但對于有著巨型分支的網(wǎng)絡而言他們并非必要條件,只需要每個人有一個以上的連接就足夠了。
這樣的網(wǎng)絡達到的連通性給廣泛的傳染提供了可能。
相變與基本再生數(shù)
“相變”(phase transition)這一術(shù)語經(jīng)常用在熱力學中,意思指物質(zhì)形態(tài)的改變。例如當水變成冰或水蒸氣時,我們就說發(fā)生了相變。
人類網(wǎng)絡也在發(fā)生相變,從孤立節(jié)點和小型分支的聚集,到包含由相當比例的節(jié)點構(gòu)成的巨型分支,并最終形成所有節(jié)點都能通過網(wǎng)絡路徑連接的形態(tài)。網(wǎng)絡中的聯(lián)系所占比例的增加,就好比隨著溫度的提高,把冰變成水,再變成水蒸氣。
相變的一個醒目特征是其發(fā)生可以非常突然。溫度略低于冰點時,你還站在冰上,而提高1度之后,你就掉進了水里。類似的是,網(wǎng)絡中聯(lián)系頻率的微小改變可以對其組成結(jié)構(gòu)產(chǎn)生巨大效應。圖2描繪了這種情況。隨著每個人的平均朋友數(shù)從0.5人[圖(a)]增加到1.5人[圖(b)],我們從一個基本沒有連接的網(wǎng)絡跨越到一個大多數(shù)人能相互連通的網(wǎng)絡。聯(lián)系頻率的進一步小幅提高[圖(c)和圖(d)]使之成為“路徑連通”或簡稱“連通”的網(wǎng)絡:其中的每個人都能通過網(wǎng)絡路徑實現(xiàn)彼此聯(lián)系——圖(c)處于近似連通狀態(tài),還有兩個節(jié)點未被連上。
網(wǎng)絡的相變對疾病控制具有基礎性的意義。與疾病及可能傳播疾病的網(wǎng)絡有關的一個關鍵數(shù)字是疾病的“基本再生數(shù)”(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其含義是一個典型的感染者會讓多少其他人受到新的感染。若基本再生數(shù)大于1,則疾病會蔓延,若小于1,則疾病會消亡。
基本再生數(shù)的臨界值為1,對應圖2所示的網(wǎng)絡出現(xiàn)巨型分支的相變情形。背后的原理極簡單卻很關鍵:每個感染者造成的新感染多于1個,傳染就會繼續(xù)擴大,每個新感染會造成更多人被感染,使其不會停止。而低于臨界值時,傳染過程會走向衰減。用網(wǎng)絡的術(shù)語講,如果每個人有1個以上的朋友,則這個分支會向外生長,擴展為一個巨型分支。如果平均朋友數(shù)小于1,網(wǎng)絡將成為大量互不連接的小型分支與孤立節(jié)點的集合。這與物種繁殖(再生)有著明顯的相似性:如果一個社會中每個成年人的平均子女數(shù)多于1,如此循環(huán),社會將成長壯大。如果每個成年人的平均子女數(shù)小于1,社會將走向萎縮。
圖2 不同平均度數(shù)的網(wǎng)絡對比。如圖(a)所示,每個節(jié)點的連接少于1的網(wǎng)絡處于零散狀態(tài)。一旦如圖(b)那樣,每個節(jié)點的平均連接數(shù)大于1,就會連接成一個巨型分支:圖(b)右下方通過路徑能夠彼此相連的很大一群節(jié)點。每個節(jié)點的平均連接數(shù)繼續(xù)稍有增加,會使幾乎所有節(jié)點被聯(lián)系起來,如圖(c)所示。最終導致網(wǎng)絡實現(xiàn)完全的路徑連通,任意兩個節(jié)點都有路徑能連接起來,如圖(d)所示。
我們很容易找出某個種群的再生數(shù)由于環(huán)境的關系,降低到每個成年個體的生存后代數(shù)量低于1,使其走向滅絕或接近滅絕的例子。美洲野牛的數(shù)量在18世紀可能超過5000萬頭,到19世紀末只剩下約500頭。它們的再生數(shù)在南北戰(zhàn)爭后急劇減少,因為新建的鐵路線帶來了更多的獵人,也更容易把獸皮運出去。槍支的改進讓獵人可以在很遠距離外殺死一頭野牛,并且不會驚擾整個獸群,例如19世紀70年代開發(fā)出的“大50式”夏普斯步槍擁有四分之一英里(超過400米)的可靠射程。大平原印第安人評價說:這種槍是“用在今天,毀了明天”。獵人數(shù)量的增加,槍支的改進,每人殺掉更多的野牛,更快地把戰(zhàn)利品運出去,讓野牛的死亡速度遠遠超出了繁殖速度。北美野牛的再生數(shù)量快速下跌,原有的種群在幾十年里幾乎被消滅殆盡。
疾病的基本再生數(shù)取決于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的傳播有多容易,以及每個人有多少人際聯(lián)系。因為不是每個聯(lián)系都會傳染疾病,基本再生數(shù)通常低于網(wǎng)絡中的平均度數(shù)。再生數(shù)根據(jù)不同的病種和地點存在差異。
西非埃博拉疫情
埃博拉病的基本再生數(shù)(在沒有醫(yī)療干預時)據(jù)估計在幾內(nèi)亞和利比里亞略高于1.5,在塞拉利昂則接近2.5。這一差異源于人口密度的不同,它影響了人們每天平均接觸的其他人的數(shù)量,塞拉利昂的人口密度比幾內(nèi)亞和利比里亞高出約60%。
相較之下,麻疹的再生數(shù)比埃博拉病高得多,因為它不是通過血液和唾液,而是由懸浮顆粒傳染。根據(jù)當?shù)氐娜丝诿芏扰c接觸頻率,再生數(shù)可達到12——18。麻疹對于未接種疫苗的人群而言非常危險。白喉、流行性腮腺炎、小兒麻痹癥和風疹等疾病的再生數(shù)介于其間,為4——7。
疾病再生數(shù)的差異對應著不同的網(wǎng)絡環(huán)境。艾滋病毒(HIV)要通過親密接觸才能傳染。而只需要一次握手,或者在汽車或飛機上坐在咳嗽的人附近,就能讓人們?nèi)旧狭鞲小S纱藢е略诹鞲袀鞑ゾW(wǎng)絡中存在太多的人際連接,而艾滋病傳播網(wǎng)絡中的連接數(shù)較少。然而這并不意味著艾滋病不會傳播,它在世界上某些地區(qū)和某些人群中的再生數(shù)遠遠高于1,因此在全球的許多社群中依然相當常見。
再生數(shù)是免疫政策的核心。疫苗并不需要完全有效,或者接種到每個個體,才能阻止疾病的廣泛傳播,它只需要把再生數(shù)降低到1以下即可。接種疫苗不僅能保證接種者的安全,而且阻斷了他們在傳播網(wǎng)絡中的聯(lián)系,由此降低了社會中的疾病再生數(shù),有利于保護其他人群。假如開始時的疾病再生數(shù)為2,每個感染者平均會傳染2個人,那么只需給略超過一半的人口接種疫苗,就會使疾病再生數(shù)低于1,從而限制疾病的蔓延。





